- 相關推薦
法律是一種理性對話
法律向來被認為是一種主權意志的命令。對于任何一個進入文明狀態的社會而言,法律都是政治統治的必要手段,而社會基本關系正因為這種統治才得以存在與維持。在歷史上,作為命令的法律,甚至讓西方最偉大的哲人甘愿為一項在他看來顯然不公的裁決而獻身。早在中國的孔子時代,西方雅典的陪審團曾以蠱惑青少年褻瀆神靈的罪名,兩次把公認的“智者”蘇格拉底判處死刑。在公開辯論中,蘇格拉底為自己的權利據理力爭,但終究無濟于事。他選擇尊重雅典公民的判決,平靜地喝下了送來的毒鴆。如果說就某特定國度的特定時期而言法律是命令,那么把它放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考察,法治社會的法律又是一種永恒的理性對話過程。它是一種“對話”(discourse),乃是指法律是在各種不同的觀點及利益的交鋒與辯論中不斷獲得產生、變更與發展;它是一種“理性”(retional)對話,乃是指這種對話在本質上是一種平和而非暴力的說理過程。通過理性說服與辯論,具有不同利益與觀點的人們在探索公共利益的過程中達成某種妥協,并使成為法律條文;在法律獲得某種方式的實施之后,對它所產生的社會效果又會出現見仁見智的理解,于是又對這項法律的廢存或修改進行新一輪的對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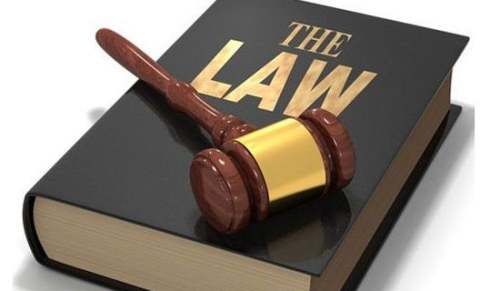
因此,從長遠來看,法律處于不斷的發展與變化過程,而在法治國家內,這是一種主要通過對話而進行的過程。
事實上,對話的存在與否,乃是使法治區別于專制和人治的重要標準。專制和人治一脈相承,因為專制-無論是多數人還是少數人的專制-最后都取決于一種和社會公共利益無關的任意意志。在專制國家里,法律是統治者意志的直接表示;根據統治者的喜怒好惡,這種意志未經任何廣泛的質疑與辯論而直接強加于社會。相反,在法治社會,法律的最終目的在于促進公共利益,而非以犧牲社會普遍利益為前提的個人或特定團體的利益,且任何個人或集團都沒有權力獨斷“公共利益”的定義。究竟什么是“公共利益”?它如何能以社會代價最小的方式而獲得有效實現?它的實現要求制定什么樣的法律?這些問題都必須獲得自由、廣泛與公開的討論,且不同意見并不因其與社會主流格格不入而受到壓制,而是被給予充分機會以證明其合理性,甚至法律本身會反映這些不同意見的部分要求。因此,盡管無論在專制還是法治下,具備實際效力的法律都必然帶有權威性,但如果法律失去了對話,那么它就只能是專制而非法治的產物。法治和專制的根本區別,就在于法律不只是一種強制權力的運用,而更是一種平和理性的以陳述理由為主的說服過程。
在法治國家里,這種法律的對話是由許多主體參與、以多種方式進行的過程。在此只想說明這個過程經常被忽視的一個方面:即在法院-尤其是具有判例法傳統的法院-內進行的對話。一般認為,法院是一個發布判決的地方,而在法治國家,司法判決構成了必須獲得有效執行的命令。但另一方面,法院又首先是一個說服、評理的地方,在法院內進行的辯論無疑是法律對話的一部分。在一個具體的爭議中,帶有不同利益和觀點的當事人通過其法律代理人,在法官面前爭取對各自最有利的法律解釋。法官則盡可能站在中立的位置上總結當事人雙方的論點,并作出自己認為對社會最佳的判斷。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個個零散的案例積累起一整套法律規則,法官們在實際判案中憑經驗制作的一塊塊磚瓦慢慢造成判例法體系的宏偉大廈。
和成文法不同的是,英美等法治國家的判例法同時記錄著多數與少數意見。在這里,少數意見的理由獲得了更完整的闡述與尊重。在一個具體案例中,多數意見“獲勝”了,因而形成了具有約束力的法律。少數意見固然因暫時“失敗”而沒有法律效力,但并不因此而受到忽略。因為少數意見完全可能包含著真理的智慧。今天的少數意見,很可能若干年后成為多數意見;原來被認為是錯誤的觀點,后來卻被證明是正確的。少數法官對某一法律問題所持的當時未獲多數認同的意見,很可能成為未來法律改革的萌芽,并為法律的平穩嬗變提供理論基礎。這種現象在西方國家的法治史上是不乏先例的,僅美國最高法院對聯邦憲法的解釋就提供了豐富的例證。
普通法繼承了蘇格拉底在西方思想上所開創的理性對話傳統,它表現了依靠平等、說服與獨立思維-而非強力與個人意志-去解決社會爭端的精神。當然,蘇格拉底本人為他所倡導的對話付出了生命代價。但這一永恒的歷史教訓告誡后人,無論何種形式的權力與意志-甚至是多數人按合法程序表達的意志
[1] [2]
【法律是一種理性對話】相關文章:
清華招生新政是一種理性糾偏04-28
如何理性認識郵政法律糾紛04-28
認識的理性與非理性04-28
論宗教理性和道德理性對理性的異化04-30
關于80年代一種反理性話語的重提04-29
論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04-27
經濟理性與道德理性的困境與反思04-26
理性的作文09-27
科學與理性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