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關推薦
語文常談7
7.四方談異漢語有多少方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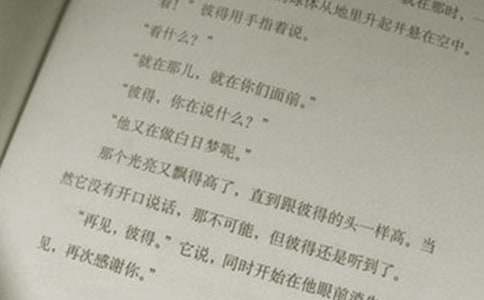
每一個離開過家鄉的人,每一個有外鄉人的市鎮或村莊的居民,都曾經聽見過跟自己說的話不一樣的外鄉話。在象上海這樣的“五方雜處”的城市,差不多每個人都有機會跟說外鄉話的人打交道。比如有一家無錫人搬來上海住,他們家里說的是無錫話,他們家里請的保姆說的是浦東話,他們樓上住著一家常州人,說的是常州話,隔壁人家是廣東來的,說的是廣州話,弄堂口兒上“煙枝店嬸嬸”說的是寧波話。他們彼此交談的時候,多半用的是不純粹的上海話,也許有幾個老年人還是用他們的家鄉話,別人湊合著也能懂個八九成(除了那位廣東老奶奶的話)。他們在電影院里和收音機里聽慣了普通話,所以要是有說普通話的人來打聽什么事情,他們也能對付一氣。這些人家的孩子就跟大人們有點不同了,他們的普通話說得比大人好,他們的上海話更加地道,那些上過中學的還多少懂幾句外國話,在他們的生活里,家鄉話的用處越來越小了。──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全國人民至少是大城市居民的既矛盾而又統一的語言(口語)生活。
大家都知道漢語的方言很多,可究竟有多少呢?很難用一句話來回答。看你怎樣給方言下定義。如果只要口音有些不同,就算兩種方言,那就多得數不清,因為有時隔開十里二十里口音就不完全一樣。要是一定要語音系統有出入(甲地同音的字乙地不同音,而這種分合是成類的,不是個別的),才算不同的方言,大概會有好幾百,或者一二千。要是只抓住幾個重要特點的異同,不管其他差別,那就可能只有十種八種。現在一般說漢語有八種方言就是用的這個標準。這八種方言是:北方話(從前叫做“官話”)、吳語、湘語、贛語、粵語、客家話、閩南話、閩北話。①實際上這北方話等等只是類名,是抽象的東西。說“這個人說的是北方話”,意思是他說的是一種北方話,例如天津人和漢口人都是說的北方話,可是是兩種北方話。只有天津話、漢口話、無錫話、廣州話這些才是具體的、獨一無二的東西:只有一種天津話,沒有兩種天津話。寧可把“方言”的名稱保留給這些個“話”──剛才說了,漢語里大概有好幾百或者一二千,──把北方話等等叫做方言區。一個方言區之內還可以再分幾個支派,或者叫做方言群,比如北方話就可以分華北(包括東北)、西北、西南、江淮四大支。
──────
① 這些名稱有的用“話”,有的用“語”。有些學者嫌這樣參差不好,主張一律稱為方言:北方方言、吳方言等等。能夠這樣當然很好,不過舊習慣一時還改不過來。
方言語匯的差別
方言的差別最引人注意的是語音,劃分方言也是主要依據語音。這不等于不管語匯上和語法上的差別。事實上凡是語音的差別比較大的,語匯的差別也比較大。至于語法,在所有漢語方言之間差別都不大,如果把虛詞算在語匯一邊的話。
現在引一段蘇州話做個例子來看看。①
俚走出弄堂門口,叫啥道天浪向落起雨來哉。
他走出胡同口兒,誰知道天上下起雨來了。
啊呀,格爿天末實頭討厭,吃中飯格辰光,
阿呀,這種天么實在討厭,吃午飯的時候,
還是蠻蠻好格 ,那?K會得落雨格介?
還是很好很好的呀,怎么會下雨的呀?
又弗是黃梅天,現在是年夜快哉呀!
又不是黃梅天,現在是快過年啦!
這里可以看出,蘇州話和普通話在語匯上是很有些差別的。可是語法呢?拋開虛詞,這里只有兩點可說,蘇州話的“蠻”相當于普通話的“很”,可是蘇州話可以說“蠻蠻”(加強),普通話不能說“很很”;蘇州話說“年夜快”,普通話說“快過年”,語序不同。當然不是說蘇州話和普通話在語法上的差別就這一點兒,可是總的說來沒有什么了不起。語匯方面有兩處需要說明:一,不是任何“口兒”蘇州話都叫“門口”,這里寫的是上海的事情,上海的里弄口兒上都有一道門,所以說“弄堂門口”。二,不是所有的“這種”蘇州話都說“格 ”,只有意思是“這么一種”并且帶有不以為然的口氣的“這種”才說成“格 ”。
比較方言的語匯,首先要區別文化語匯和日常生活語匯。文化語匯,特別是有關新事物的用語,各地方是一致的,有例外也是個別的。比如下面這句話:“做好農田基本建設工作,有計劃有步驟地把旱田改造成水田,把壞地改造成好地,是從根本上改變這些地區的自然面貌,擴大穩定高產農田面積的重要措施”,方言的差別只表現在“把”、“是”、“的”、“這些”等虛詞上,在實詞方面是沒有什么差別的。
比較方言的語匯,還應當特別注意:別以為都是一對一的關系,常常是一對多乃至多對多的關系(幾個一對多湊在一塊兒)。比如語氣詞,每個方言都有自己的語氣詞系統,兩個方言之間常常是不一致的。不但是虛詞,實詞方面也不見得都是一對一。魯迅的小說《社戲》里寫阿發、雙喜他們偷吃田里的羅漢豆,這羅漢豆是紹興方言,別處叫蠶豆,紹興話里也有蠶豆,可那是別處的豌豆。又如鐘和表,南方的方言都分得很清,可是北方有許多方言不加分別,一概叫做表。又比如你聽見一個人說“一只椅子四只腳”,你會以為他的方言里只有“腳”,沒有“腿”,管腿也叫腳。其實不然,他的方言跟你的方言一樣,腿和腳是有分別的,只是在包括這兩部分的場合,你用“腿”概括腳,他用“腳”概括腿罷了。還有比這更隱晦的例子。比如兩個朋友在公園里碰見了,這一位說:“明兒星期天,請你到我們家坐坐。”那一位說:“我一定去。”這一位聽了很詫異,說:“怎么,你倒是來不來呀?”他詫異是因為按照他的方言,他的朋友應該說“我一定來”。
──────
①引自倪海曙的蘇州話小說《黃包車》,收入作者的《雜格嚨咚集》(1950)。
主要的語音分歧
漢語方言的語音差別是很大的。上面那一段蘇州話,用漢字寫下來,你雖然不是吳語區的人,也能懂個十之八九。可要是讓一個蘇州人說給你聽,管保你懂不了三成。撇開語調不談,單就字音來比較,我們可以指出漢語方言中間主要有哪些分歧。漢語字音是由聲、韻、調三個成分構成的,這三方面都有一些影響面比較大的分歧點。但是在談到這些特點以前,得先知道音類分合和音值異同的區別。最好拿聲調來做例子。普通話只有四聲,蘇州話卻有七聲,這里顯然有調類分合的問題。可是同是陽平聲的字(如“前”、“年”),普通話是高升調,蘇州話是低升調,聽起來不一樣,這只是調值不同,不關調類的事。再舉個韻母的例子。比如蕭豪韻的字,在普通話里是一個韻(ao,iao),在吳語區方言里也都是一個韻,可是這個韻母的音在這些方言里不一致,其中也很少是跟普通話相同的;這也只是音值的問題,不是音類的問題。我們要談的語音分歧是音類上的,不是音值上的。下面列舉一些主要的分歧。有一點需要先在這里交代一下:這里指出來的某某方言區有某某特點,都是就大勢而論,常常有部分方言是例外。
(1)有沒有濁聲母。這里說的濁聲母指帶聲的塞音、塞擦音、擦音,不包括鼻音和邊音。漢語方言里只有吳語和一部分湘語有濁聲母,在這些方言里,舉例來說,“停”和“定”是一個濁聲母,跟“聽”的聲母不同,跟“訂”的聲母也不同。這種濁聲母在各地方言里變化的情況如下(用dh代表上面說的那個濁聲母):
吳,湘部分,閩部分
湘部分,閩部分
北,粵
客,贛
(2)在-i和-¨ 前邊分不分z-,c-,s-和j-,q-,x-(或g-,k-,h-),例如“酒、秋、想”等字和“九、邱、響”等字是否聲母相同。①閩語,粵語,客家話,吳語,少數北方話(20%),少數湘語,少數贛語有分別。多數北方話(80%),多數湘語,多數贛語無分別。
(3)分不分z-,c-,s-和zh-,ch,sh-,例如“資、雌、絲”等字和“知、癡、詩”等字是否聲母相同。多數北方話(華北、西北的大多數,西南、江淮的少數),湘語,一部分贛語,一部分客家話分兩套聲母,但是字的歸類不完全相同,有些字在某些方言里是zh-,ch-,sh-,在另一些方言里是z-,c-,s-。閩語,粵語,吳語,一部分贛語,一部分客家話,少數北方話(西南、江淮的多數)只有一套聲母,發音絕大多數是z-,c-,s-。
(4)分不分n-和l-,例如(一)“腦、難”和“老、蘭”是否聲母相同,(二)“泥、年”和“犁、連”是否聲母相同。
(一)(二)都分 粵,客,吳,北多數
(一)不分,(二)分 湘,贛,北(西北少數,西南少數)
(一)(二)都不分 北(西南多數,江淮多數)
閩語分n-和l-,但是字的歸類跟上面第一類方言不完全一致,閩北話比較接近,閩南話很多字由n-變成l-。
(5)n-,ng-和零聲母的分合。可以把有關的字分四類來看。
(一)“礙、愛、耐”是否聲母相同。
礙ng- ≠ 愛O- ≠ 耐n- 閩,粵,客,吳
礙ng- = 愛ng- ≠ 耐n- 贛,湘部分,北部分
礙O- = 愛O- ≠ 耐n- 湘部分,北部分
礙n- = 愛n- = 耐n- 北少數
(二)“牛”和“扭”是否聲母相同。
牛ng- ≠ 扭n- 粵
牛ng-/g- ≠ 扭n-/l- 閩
牛n-/gn- = 扭n-/gn- 其余
(三)“誤”和“惡”(可惡)是否聲母相同。
誤ng- ≠ 惡O- 閩,粵,客,吳,湘部分
誤O- = 惡O- 北,贛,湘部分
(四)“遇”和“裕”是否聲母相同。
遇ng-/gn- ≠ 裕O- 閩,客,吳,湘部分
遇O- = 裕O- 北,粵,贛,湘部分
(6)分不分-m,-n,-ng,例如“侵、親、清”是否韻尾相同,“沉、陳、程”是否韻尾相同。
侵-m≠親-n≠清-ng 粵,閩南
侵-n=親-n≠清-ng 北(華北,西北部分)
侵-m≠親-n=清-n 客
侵=親=清(皆-n/-ng) 吳,湘,贛,閩北,北(江淮,西南,西北部分)
客家話的-m韻尾只保存在一部分字里,另一部分字已經變成-n。
(7)有沒有韻母和介母¨ 。有些方言沒有¨ 這個音,有些方言用到¨ 音的字數比別的方言少。這些方言一般是用i去代 ,造成“呂、李”同音,“需、西”同音,“宣、先”同音,在一定條件下也用u代 ,造成“宣、酸”同音,“云、魂”同音,“君、昆”同音。各地方言比較,華北北方話有¨ 音的字最多,西北、西南、江淮北方話都有些方言減少一部分字,甚至完全沒有¨ 音(如南京話、昆明話)。北方話之外,在¨ 音字的多寡上,贛語很接近華北,其次是粵語,又其次是吳語,湘語,閩北話。客家話和閩南話完全沒有¨ 音,粵語等也有個別方言完全沒有¨ 音。
(8)有沒有入聲。北方話之外的方言都有入聲,北方話也有一部分方言有入聲。有入聲的方言,入聲的發音分三類:(一)粵語,贛語,客家話、閩南話,分別-b,-d,-g三種塞音韻尾;(二)吳語,閩北話,某些北方話(主要是江淮話),沒有這種分別,只有一個喉塞音;(三)湘語,某些北方話(主要是少數西南話),沒有特殊韻尾,只是自成一種聲調。沒有入聲的方言,對于古代入聲字的處理可以分兩類:(一)全部并入另一聲調(多為陽平),大多數西南方言屬于這一類。(二)分別轉到陰平、陽平、上聲、去聲,或其中的兩聲、三聲,大多數華北和西北方言屬于這一類。
別的分歧還有不沙,但是有的影響面較小,有的情況復雜,不容易簡單說明,這里都不說了。
──────
① 一般所說尖音和團音的分別,專指zi,z¨ 等音和ji,j 等音的分別,不涉及gi,g¨等音。
方言和方言之間的界限
無論是語音方面還是語匯方面,方言和方言之間的界限都不是那么整齊劃一的。假如有相鄰的甲、乙、丙、丁四個地區,也許某一特點可以區別甲、乙為一方,丙、丁為一方,另一特點又把甲、乙、丙和丁分開,而第三個特點又是甲所獨有,乙、丙、丁所無。比如在江蘇省東南部和上海市的范圍內,管“東西”叫“物(音‘末’)事”的有以啟東、海門、江陰、無錫為邊界的二十一個縣、市;管“鍋”叫“鑊子”的地區基本上相同,但是江陰說“鍋”;管“鍋鏟”叫“鏟刀”的,除上面連江陰在內的地區外,又加上鄰近的常州、揚中、泰興、靖江、南通市、南通縣六處;管“肥皂”叫“皮皂”的,又在原地區內減去啟東、海門兩處,加上常州一處;如此等等。
如果在地圖上給每一個語音或語匯特點畫一條線──方言學上叫做“同言線”,──那末兩個方言之間會出現許多不整齊的線,兩條線在一段距離內合在一起,在另一段又分開了。請看下頁的圖。
昌黎-盧龍-撫寧地區方言圖①
圖 例
……線以北,“愛、襖、暗、岸”的聲母是n,分別跟“耐、腦、難(災難)”同音;線以南,“愛、襖、暗、岸”的聲母是ng,不跟“耐”等同音。
-?-?-線以北,兒韻和兒化韻都不卷舌;線以南都卷舌。
----(1)線以北,“頭?上,黃?瓜”的“頭、黃”跟單說的“頭、黃”同聲調;線以南不同聲調。
(2)線以北,“沒錢”的“沒”跟“沒來”的“沒”同音;線以南,不同音。
~~~線以北,“腌菜”的“腌”的聲母是零;線以南是r。
-??-??線以北,管啄木鳥叫“?e(qiān)?e木”;線以南,管這種鳥叫“?e得木”、“?e搭木”或“?e刀木”。
從圖上可以看出,這個地區的話可以分成兩個方言,這是不成問題的,可是在哪兒分界就不是那么容易決定了。
不但方言和方言之間是這種情況,方言區和方言區之間也是這種情況,象前邊說過的“物事”、“鑊子”、“鏟刀”、“皮皂”,都屬于吳語的詞匯,可是分布的廣狹就不一致。甚至相鄰的親屬語言之間,如南歐的羅馬系諸語言之間,東歐的斯拉夫系諸語言之間,也都有這種情況。單純根據口語,要決定是幾種親屬語言還是一種語言的幾種方言,本來是不容易的。事實上常常用是否有共同的書面語以及跟它相聯系的“普通話”來判斷是不是一種語言。比如在德國和荷蘭交界地方的德語方言,跟荷蘭語很相近,跟德國南方的方言反而遠得多。德語作為一個統一的語言,跟荷蘭語不相同,主要是由于二者各自有一個“普通話”。在沒有文字的情況下,語言和方言就很不好區別。這也就是對于“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種語言?”這個問題難于作確定的回答的原因。
方言調查對于語言史的研究很有幫助。古代的語音語匯特點有的還保存在現代方言里,例如吳語和湘語里的濁聲母,閩語、粵語、客家話里的塞音韻尾(-b,-d,-g)和閉口韻尾(-m)。(更正確點應該說是我們關于古音的知識很大一部分是從比較現代方言語音得來的。)現代已經不通用的語詞很多還活在方言里,例如“行”、“走”、“食”(閩、粵、客,=走、跑、吃),“飲”(粵,=喝),“著”(粵、吳,=穿衣),“面”、“翼”、“曉”(閩、粵,=臉、翅膀、知道),“箸”(閩、客,=筷子),“晏”、“新婦”(閩、粵、吳,=晚、兒媳婦),“目”、“啼”、“糜”、“湯”、(閩,=眼睛、哭、粥、熱水),等等。這些都是原來常用的詞,原來不常用,甚至只是記載在古代字書里的,在方言里還可以找到不少。但是一定要詞義比較明細,字音對應合乎那個方言的規律,才能算數。否則牽強附會,濫考“本字”,那是有害無益的事情。
漢語從很早以來就有方言。漢朝的楊雄編過一部《??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后代簡稱為《方言》,記錄了很多漢朝的方言詞。按照這部書的內容,漢朝的方言大致可以分成十一區:秦晉、趙魏、燕代、齊魯、東齊青徐、吳揚越、衛宋、周韓鄭、汝潁陳楚、南楚、梁益。但是楊雄的書只管方“言”,不管方“音”,所以看不出這些地區的語音是怎樣不同。后來續《方言》的書很不少,可惜那些作者都只著重在古書里考求方言詞的“本字”,不注重實地調查,不能反映方言的分布情況。因此一部漢語方言發展史研究起來就很困難。要說各地方言古今一脈相承,顯然不大可能,因為居民有遷徙(歷史上有很多大量遷徙的記載),方言也有消長。也有人以為現代方言都出于古代的一種有勢力的方言,這也不近情理,因為在封建社會的條件下,不可能有一種方言的力量能夠把別的方言徹底排除。
──────
①這個圖是根據《昌黎方言志》(1960,科學出版社)里的方言圖重畫的。圖的范圍是調查時間(1959)的河北省昌黎縣縣界,比現在的縣界(也是1958年以前的舊界)大,包括現在的昌黎全縣(圖里的南部),盧龍縣的一部分(圖里的西北部),撫寧縣的一部分(圖里的東北部)。這里用昌黎地區的方言圖做例子,因為這是唯一的調查點比較密的材料,其他材料大都是一縣調查一兩點,點與點之間距離太大,同言線不好畫。
要推廣普通話
在一種語言沒有“普通話”的情況下,方言只有一個意義,只是某一語言的一個支派。要是這種語言有了一種“普通話”,“方言”就多了一層跟“普通話”相對待的意思。“普通話”的形成跟書面語的產生和發展有關系。書面語以某一方言為基礎,同時又從別的方言乃至古語、外語吸收有用的成分。基礎方言本身的變化反映在書面語上,而通過書面語的使用和加工,基礎方言又得到了擴大和提高,漸漸成為一種“普通話”。可見“普通話”和書面語是互相影響,互相促進的。古代漢語有沒有“普通話”?也可以說是有,也可以說是沒有。古代有所謂“雅言”,楊雄的書里也常常說某詞是“通語”、“四方之通語”。這些“通語”多半是見于書面的,可是未必有統一的語音,也未必能構成一個比較完整的語匯(也就是說,在當時的語匯里還有一部分是“語”而非“通”,有一部分是“通”而非“語”)。加上從漢朝起書面語漸漸凝固下來,走上跟口語脫節的道路。因此,盡管每個時代都有一兩種方言比別的方言有更大的威望,①可是不容易產生一種真正的普通話。一直要等到一種新的書面語即所謂“白話”興起之后,才再度提供這種可能,并且經過幾百年的發展,終于由可能變成現實。
事物的發展大都決定于客觀的形勢。我們現在不能再滿足于“藍青官話”,而要求有明確標準的“普通話”,不能再滿足于這種普通話只在某一階層的人中間通行,而要求它在全民中間逐步推廣,這都是由我們的時代和我們社會的性質決定的。推廣普通話的重要性已經為多數人所認識,不用我再在這里多說。我只想提一兩件小事情,都是自己的切身經驗。五十年前初到北京,有一天是下雨天,一個同住的南方同學出門去。他用他的改良蘇州話向停在馬路對面的洋車連叫了幾聲“w¨ngb?jū”(“黃包車”,他以為“車”該說jū),拉車的只是不理他,他不得不回來搬救兵。公寓里一位服務員走出去,只一個字:“chē!”洋車馬上過來了。另一件事是我第一次看《紅樓夢》的時候,看到史湘云行酒令,拿丫頭們開玩笑,說:“這鴨頭不是那丫頭,頭上哪討桂花油?”覺得這有什么可笑的,“鴨”[a?]頭本來不是“丫”[o]頭??。其實這樣的例子多得很:“有什么福好享?有個豆腐!”“騎驢來的?──不,騎鹿(路)來的。”這些都是普通話里同音而很多方言里不同音的。當然這些都是很小的小事情,不過既然在這些小事情上不會普通話還要遇到困難,在大事情上就更不用說了。
方言地區的人怎樣學習普通話?最重要的還是一個“練”字。懂得點發音的知識,對于辨別普通話里有而家鄉話里沒有的音,象zh-,ch-,sh-和z-,c-,s-的分別,n-和l-的分別,-n和-ng的分別,自然有些用處,然而不多多練習,那些生疏的音還是發不好的。至于哪些字該發zh-的音,哪些字該發z-的音,哪些字是n-,哪些字是l-,如此等等,更加非死記多練不可。有時候能從漢字的字形得到點幫助,例如“次、瓷、資、咨、諮、姿、姿”是z-或者c-,“者、豬、諸、煮、箸、著、褚、儲、躇”是zh-或者ch-。可是這只是一般的規律,時常會遇到例外,例如“則、廁、側、測、惻”都是z-或者c-,可是“鍘”卻是zh-。又如“乍、炸、詐、榨”都是zh-,可是“作、昨、柞、怎”又都是z-,這就更難辦了。(這個例子碰巧還是有點規律,凡是a韻的都是zh-,不是a韻的都是z-。)
推廣普通話引起怎樣對待方言的問題。“我們推廣普通話,是為的消除方言之間的隔閡,而不是禁止和消滅方言。”②普通話逐步推廣,方言的作用自然跟著縮小。學校里的師生,部隊里的戰士,鐵路和公路上的員工,大中城市的商店和服務行業的工作人員,為了實際的需要,都會學會說普通話。在一些大城市里,很可能在一個家庭之內,老一代說的是方言。第二代在家里說方言,到外面說普通話,第三代就根本不會說或者說不好原來的“家鄉話”。但是盡管使用范圍逐漸縮小,方言還是會長期存在的。普通話為全民族服務,方言為一個地區的人服務,這種情況還會繼續很長一個時期。在不需要用普通話的場合,沒有必要排斥方言,事實上也行不通。甚至“只會說普通話的人,也要學點各地方言,才能深入各個方言區的勞動群眾”。③
但是這不等于提倡用方言。比如用方言寫小說,演話劇,偶一為之也無所謂,可不必大加推崇,廣為贊揚,認為只有用方言才“夠味兒”。普通話也是挺夠味兒的。
──────
①六世紀末,《顏氏家訓》的作者顏之推評比當時方音,說:“?n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他主要是講書面語里的字音,而且不但“參校方俗”,還要“考??古今”,所以他的評價不完全是根據實際形勢,但是大概也是符合實際形勢的。九世紀的胡曾有《嘲妻家人語音不正》詩:“呼‘十’卻為‘石’,喚‘針’將作‘真’,忽然云雨至,卻道是天‘因’。”可見那時候也有公認的“正”音。
②周恩來:《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1958年1月10日在政協全國委員會舉行的報告會上的報告。
③周恩來:《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1958年1月10日在政協全國委員會舉行的報告會上的報告。
8.文字改革
漢字能滿足我們對文字的要求嗎?
語言是一種工具,文字代表語言,當然更加是一種工具。一種工具要是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務,就得加以改進或改革。有時候一種文字,由于這種或那種原因,不能很好地代表語言,于是產生改革的需要,在世界文字史上是數見不鮮的事情。土耳其文原先用阿拉伯字母,不適合土耳其語的語音結構,在本世紀二十年代改用拉丁字母。朝鮮和越南原先用漢字,現在都用拼音文字。日本文原先以漢字為主體,搭著用些假名(音節字母),現在以假名為主體,搭著用些漢字。我們現在用的漢字是不是適應現代漢語的情況,能不能滿足我們對文字的要求,要不要改革,怎樣改革,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
文字問題不能脫離語言問題來考慮。在歷史上,漢字改革問題一直是漢語文改革問題的一部分。
六十年前,當我還是個小學生的時候,我國人民使用語言文字的情況跟現在是不相同的。那時候,一個人從小學會了說本地話,六歲上學讀文言書──《論語》、《孟子》或者《國文教科書》,看你進的是哪路學堂,──也學著寫文言文。說話和讀書各管一方,有些聯系,但是很不協調。比如你學了許多漢字,可那只能用來寫文言,要用它寫本地話就有許多字眼寫不出。
一個人要是一輩子不離開家鄉,自然不會發生語言問題。可要是上外地去上學,或者去當學徒,或者去做買賣什么的,家鄉話就常常不管用了。到哪里得學哪里的話,除非你家鄉話跟那里的話差別不大,能湊合。我上的中學是江蘇省第五中學,在常州,老師有常州人,有蘇州人,有宜興人,有江陰人,有無錫人,有靖江人,說的話全跟我的家鄉丹陽話不一樣。頭一個星期我上的課全等于沒上,一個月之后還有一位動物學老師的話只懂得一半。那時候還沒有什么“國語”,就是后來有了“國語”,也只是在小學生中間鬧騰鬧騰,社會上一般人很少理會它,因為在吳語區它的作用還趕不上一種方言。比如你到上海去辦事,最好是能說上海話,其次是附近幾個縣的方言。要是說“國語”,連問個路都有困難。
書面交際用文言,可是大家也都看白話小說,全是無師自通。遇到不認識的字,意思好猜,──有時候也猜不出,──字音不知道,也沒地方問。我記得在《兒女英雄傳》里第一次碰見“旮旯”兩個字,意思是懂了,可一直不知道怎么念,──這兩個字沒法子念半邊兒。
這種情況,我小時候是這樣,我父親、我祖父的時候也是這樣,大概千百年來都是這樣。大家習慣了,以為是理所當然,想不到這里邊會有什么問題,也想不出會有什么跟這不一樣的情況。
早就有人主張改革漢字
可是有人看到了另外一種情況,并且拿來跟上面的情況做比較,引起了種種疑問,提出了種種建議。遠在宋朝,就有一個人叫鄧肅說過,“外國之巧,在文書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繁,故遲。”①明朝耶穌會傳教士來華,開始用拉丁字母拼寫漢字,明末學者方以智受它的啟發,也有“如遠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的想法。到了清朝末年,中國人接觸外國事物更多了,于是興起了一種切音字運動,盧戇章、蔡錫勇、沈學、朱文熊、王照、勞乃宣等是它的代表人物。他們的時代是中國經歷了二千年封建統治,又遭受了半個世紀的帝國主義侵略,國家越來越衰弱,人民越來越困苦,改良主義的維新運動和舊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正在先后出現的時代。愛國主義喚起人們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的注意,從海陸軍備而工商實業,而科學技術,而文化教育,認識逐步深入。其中就有人看到西方強國的語文體制跟中國不大相同。他們比較中西語言文字,發現中國有三難,西方國家有三易。中國的三難是:寫文章難;認字寫字難;不同地區的人說話難。西方國家的三易是:寫文章容易,因為基本上是寫話;認字寫字容易,因為只有二三十個字母;不同地區的人說話容易,因為有通行全國的口語。于是他們提出切音字的主張,認為這是開民智、興科學的關鍵。最早的切音字運動者盧戇章的話可以代表他們的想法,他說:“竊謂國之富強,基于格致。格致之興,基于男婦老幼皆好學識理。其所以能好學識理者,基于切音為字,則字母與切法習完,凡字無師能自讀;基于字話一律,則讀于口遂即達于心;又基于字畫簡易,則易于習認,亦即易于捉筆。省費十余載之光陰,將此光陰專攻于算學、格致、化學以及種種之實學,何患國不富強也哉!”
這些切音字運動者,有的只是提出一個方案,做了一些宣傳,有的也曾開班傳授,取得一些成績,但是總的說來,他們的成就是很有限的。這主要是因為受當時政治形勢的限制:象這種以人民大眾的利益為指歸的語文改革,在人民自己取得政權以前是很難完全實現的。其次,他們對于語文改革的整個內容,以及各個部分之間的關系,或者認識不足,或者雖有認識,可是顧慮重重,不敢沖破障礙,提倡徹底改革。語文改革實際上包含三個內容:用白話文代替文言,用拼音字代替漢字,推行一種普通話。三者互相關聯,而彼此倚賴的情況不盡相同。改用白話文,不一定要用拼音字,也不需要拿普通話的普及做前提,因為有流傳的白話作品做范本。推行普通話必須有拼音的工具,但是不一定要推翻文言,可以容許言文不一致的情況繼續存在。惟有改用拼音字這件事,卻非同時推行普通話和采用白話文不可。否則拼寫的是地區性的話,一種著作得有多種版本;另一方面,如果不動搖文言的統治地位,則拼音文字始終只能派低級用場,例如讓不識字的人寫寫家信,記記零用賬。這樣,拼音字對于漢字就不能限而代之,而只能給它做注音的工具。大多數切音字運動者恰好是基本上采取了這樣一條路線,也就只能收到那么一點效果。二十多年切音字運動的總結是1913年制定、1918年公布的一套“注音字母”。
從那時候到現在,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這期間的變化可大了。白話文已經取得全面的勝利,普通話的使用范圍已經大大地擴大了,漢語拼音方案的公布也已經給拼音文字打下了可靠的基礎,雖然直到目前為止,它的主要任務還是給漢字注音。
──────
① 見周有光《漢字改革概論》,引湯金銘《傳音快字書后》。
拼音文字的優點超過缺點
為什么現在還不到全面采用拼音文字的時候呢?很顯然是因為有些條件還沒有具備:拼音的習慣還沒有普及,普通話通行的范圍還不夠廣大,拼音文字的正字法還有些問題沒有解決,如此等等。這些都是要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才能夠解決的。另一方面,大家的認識還沒有完全一致,這也是事實。大致說來,對于拼音文字有三種態度。一種態度是贊成改用拼音文字,有的人還特別熱心,恨不得立刻就實行。另一種態度是一方面承認拼音文字在某些方面勝過漢字(例如容易認,容易檢索),一方面又覺得在某些方面不如漢字(例如不能區別同音字),疑慮重重,不知道拼音文字究竟能否代替漢字。第三種態度是不贊成拼音文字,或者認為行不通,或者認為沒有必要,或者認為不利于繼承文化遺產。現在不妨把贊成的和反對的兩方面的理由拿來研究一番。
(1)漢字難學(難認,難寫,容易寫錯),拼音字好學(好認,好寫,比較不容易寫錯),這是大家都承認的。有一種意見,認為拼音不能區別同音字,老要看上下文,帶認帶猜,漢字能區別同音字,學起來雖然難些,可以一勞永逸,還是值得的。
這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拼音文字決不能象漢字的寫法,一個個音節分開,一定要分詞連寫。先學漢字后學拼音的人,總是要在腦子里把拼音字還原成漢字,就覺得它不夠明確;一起頭就學拼音文字的人,學一個詞是一個詞,并不會感覺不明確。當然,有混淆可能的同音詞仍然需要區別,也是可以想法子區別的。漢字能區別同音字,在閱讀的時候的確是一種便利。可是文字的使用有讀和寫兩個方面。寫的時候要在許多同音字里邊挑一個,這就成為一種負擔了。寫錯別字不是一直都是語文教學當中最頭疼的問題嗎?這是漢字的先天毛病,一天使用漢字,這毛病就一天不得斷根。而且一個別字為什么是別字,有時候也叫人想不通,如果你用無成見的眼光去看問題,象六七歲的孩子那樣。我家里有個六歲的孩子,學過的漢字不多,有一天寫了四個字讓我看,是“天下地一”。我告訴他“地”字錯了,該寫“第”。他問我為什么不可以寫“地”,我倒給他問住了。是啊,為什么“地”不能兼任“第”的職務呢?“地一個”,“地二個”,“地一千零一個”,在什么上下文里有誤會的可能呢?要說不讓“地”字兼差吧,為什么“輕輕地”、“慢慢地”里邊可以寫“地”呢?這可是連讀音也不一樣啊!怎么能怪孩子們想不通呢?
(2)漢字不跟實際語言保持固定的語音聯系。“學而時習之”,孔夫子說起來是某五個字音,現代的曲阜人說起來是另五個字音,北京人、上海人、廣州人說起來又各自是各自的字音。這就是說,漢字是跟抽象的漢語相聯系的,具有一種超時間、超空間的性質。反對拼音文字的人認為這是漢字的優點,改用拼音文字就得不到這種便利,各地方的人就會按照自己的方音來拼寫,別的地方的人就看不懂,現在的人寫的文章幾百年之后的人也要看不懂。至于只會拼音文字的人將要完全不能看古書,因而不能繼承文化遺產,那就更不用說了。
這個話有一定的道理,可是說這個話的人對于漢語文的目前使用情況還沒有足夠的認識。在從前,寫文章得用文言,文言既不能按某一個地方的讀音來拼寫(別處的人念不懂),更不能按古音來拼寫(各地方的人全念不下來),除了用漢字,沒有別的辦法。現在有了普通話,拼音文字拼的是普通話,不會有各行其是的問題。不錯,普通話還沒有普及,可是拼音文字也不是光有一張字母表和幾條拼寫規則,還要有課本,有詞典,可以讓不太熟悉普通話的人有個學習的工具。這樣,不但是普通話沒有普及不妨害使用拼音文字,而且使用拼音文字還可以促進普通話的普及。幾百年以后要不要修改拼法,那是幾百年以后的事情,就是修改,也沒有什么了不得。至于讀古書的問題,現在也不是不經過特殊學習就能讀古書,將來也無非把學習的時間延長一點兒罷了。而況無論現在還是將來,讀古書總是比較少數的人的事情,古書的精華總是要翻譯成現代話的。
總之,漢字、文言、方言是互相配合,相輔相成的一套工具,拼音字、白話文、普通話也是互相配合,相輔相成的一套工具。前者在中國人民的歷史上有過豐功偉績,這是不容埋沒的,但是事物有發展,形勢有變化,既然后者更能適應當前的需要,讓前者功成身退有什么不好呢?
(3)現代的工農業生產,交通運輸,科學技術,無不要求高效率,要求又快又準確。而一切部門的工作里邊都包含一部分文字工作,要是文字工作的效率提不高,就要拖后腿。在這件事情上,漢字和拼音文字的高低是顯而易見的。拼音文字的單位是字母,數目少,有固定的次序,容易機械化;漢字的單位是字,數目多,沒有固定的次序,難于機械化。字母打字比漢字打字快,打字排版比手工排版快,拼音電報比四碼電報快,用拼音字編的詞典、索引、名單比用漢字編的查起來快,還有一些新技術,象利用穿孔卡片分類、排順序、做統計,利用電子計算機查文獻、做翻譯等等,更加是很難甚至不可能用漢字進行的。
(4)現在世界上各種文字都是拼音的,只有漢字是例外,因而在我國和外國的文化交流上是一個不大不小的障礙。我們需要翻譯外國的科學、技術和其他資料,如果用拼音文字,人名、地名可以轉寫,許多國際通用的術語也可以不翻譯。現在用漢字,全得翻譯,于是譯名統一成為很嚴重的問題。而且人名、地名用漢字譯音,既不準確,又難記憶。科技術語用意譯法,對于理解和記憶是有些幫助,可是從事科學技術工作的人,除了一套漢文術語外,還免不了要記住一套國際術語,成了雙重負擔,對于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也不無影響。又如現在有很多外國朋友,為了更好地了解我國文化,吸收我國科學技術成果,很想學漢語,可是對漢字望而生畏。外國留學生都說,漢語學起來不難,他們的時間一半以上花在漢字的學習上。
總起來看,在目前的情況下,拼音文字的優點(也就是漢字的缺點)大大超過它的缺點(也就是漢字的優點),而這些缺點是有法子補救的。如果由于改用拼音文字而能把中小學的學制縮短一年,或者把學生的水平提高一級,如果由于改用拼音文字而能把文字工作的效率提高一倍到三倍──這些都是很保守的估計──那么,光憑這兩項就很值得了。
為拼音化積極準備條件
自然,在實行拼音文字以前,還有許多研究和實驗的工作要做,需要積極地做起來;坐下來等待,拼音文字是不會自己到來的。那么,現在可以做些什么工作呢?一個工作,可以辦些拼音報刊,編寫些拼音讀物,特別是兒童讀物,包括連環畫報。現在有些小學生學拼音的成績很好,可是缺少拼音讀物,英雄無用武之地。另一方面,拼音文字在正字法方面和詞匯規范方面都還存在一些問題,通過編寫拼音書刊可以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其次,可以試試在一般書刊上就一定項目試用拼音代替漢字,例如嘆詞和象聲詞。又如外國人名地名,用漢語拼音寫,可以從中總結用漢語拼音轉寫外語的規則。此外還可以多方面擴大漢語拼音的用途,如電報,科技和生產部門的代號和縮寫,盲字,教聾啞人“說話”,等等。
還有一項很重要的工作需要做,那就是思想工作。不但是對反對派要做耐心細致的說服工作,還要努力爭取中間派,消除他們的種種顧慮。有不少人,你要問他對拼音文字的意見,他說,“我承認拼音文字比漢字好,可就是如果改用拼音文字,我就要變文盲。”這種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一個人換個工作單位還要左考慮右考慮呢,何況換一個新的文字工具。可以告訴他,改用拼音文字決不是一個早晨的事情,要有一個過渡時期,即兩種文字同時并用的時期,他可能會遇到一些小小的不方便,但是變文盲是不會的。
簡化漢字只是治標
最后,談談簡化字。漢字簡化是一件好事情。一部分漢字筆劃多,形體復雜,寫起來麻煩,在群眾的筆底下早就紛紛簡化了。可是有些字你簡你的,我簡我的,互不相識,造成混亂,這就不好了。自從1956年公布經過審定的簡化字表并分批推行以來,混亂的情況基本上消滅了。是不是所有需要簡化的字都已經簡化了呢?沒有。有些需要簡化的字,象新疆的“疆”、西藏的“藏”,因為一時不能確定最好的簡化形式,暫時放一放;有些久已在群眾中間廣泛流行,象“算”簡化為“蝶”,“賽”簡化為“宀西”,因為一時疏忽,沒有列入字表。需要補充簡化的字還有相當數目,但是不會還有很多很多了。
有些同志對漢字簡化有一種片面的想法,認為簡化的字越多越好,筆劃越少越好,不但是十筆以上的字全得簡成十筆以下,就是原來已在十筆以下的字也要減它一筆兩筆。這種想法之所以是片面的,因為只看到文字需要簡易,忘了文字也需要清晰,還需要穩定。如果把所有的字都簡成十筆以下,勢必多數字集中在五筆到十筆,很多字的形象都差不多,辨認起來就費勁了,錯認的機會就增多了。更重要的是文字需要相對穩定。1956年以后印的書刊數量很大,如果現在再來一大批簡化字,就要相應地產生一大批“新繁體字”,今后的青少年念起那些書來就有一定的困難了。或者讓他們學習那些新繁體字,那是浪費人力;或者選一部分書改排重印,那是浪費物力。以后再簡化一批,就又產生一批“新新繁體字”,這樣折騰下去,什么時候能夠穩定下來呢?不斷簡化論的不足取,道理就在這里。
簡化漢字的主要目的是讓寫字能夠快些。寫字要快,本來有兩條路:可以減少筆劃,也可以運用連筆,就是寫行書。光是減少筆劃,如果還是每一筆都一起一落,也還是快不了多少。事實上我們寫字總是帶點行書味道的,但是沒有經過正規學習,有時候“行”得莫名其妙。是不是可以在學校里教教學生寫行書,讓大家有個共同的規范,可以互相認識?這里又遇到一個框框,那就是“要使印刷體和手寫體一致”。從這個原則出發,就得互相遷就,一方面在簡化漢字上搞“草書楷化”,一方面在學校里只教楷書,不教行書。為什么別種文字一般都是既有印刷體又有手寫體,大致相似而不完全相同呢?這是因為要求不同:印刷體要求容易分辨,所以有棱有角;手寫體要求寫起來快,所以連綿不斷。如果我們允許手寫體和印刷體可以在不失去聯系的條件下不完全一致,那么,有些簡化字本來是可以不去簡化它的。例如“魚”字的底下,如果書上印成四點,筆底下寫成一橫,似乎也不會出什么問題。
說來說去,簡化漢字只能是一種治標的辦法。不管怎樣簡化,改變不了漢字的本質,仍然是以字為單位,字數以千計,無固定的次序,不能承擔現代化文字工具的重任。有些人想在簡化漢字上打主意,把字形簡到不能再簡,把字數減到不能再減,用來代替拼音文字,這恐怕是徒勞的。要真正解決問題還是得搞拼音文字。(完)
【語文常談7】相關文章:
老生常談貴在常談04-25
經典常談讀書筆記02-04
經典常談心得體會02-17
經典常談朱自清閱讀心得體會02-10
也談頂真式銜接-以《經典常談》為例05-01
語文教案704-25
經典常談讀書心得02-01
小學語文《語文天地一》教案7篇01-13
語文優秀作文7篇04-14
精選語文計劃作文7篇02-03